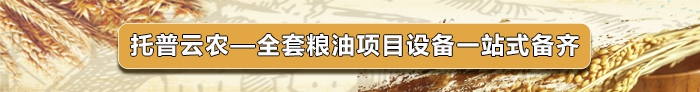保障粮食安全 到海外租地种粮
近年来,农业“走出去”在我国逐渐成为一个热门话题。2008年全球粮价涨至历史性高位时,“到海外租地种粮”的讨论更是空前热烈。今年6月,商务部网站发表了一篇题为《我国农业“走出去”要向“两端”进发》的调研文章,使这一话题再次引起了人们的关注。
尽管目前国际市场上的粮价已经回落,但世界范围内的粮食安全问题以及我国的农产品(11.43,-0.18,-1.55%)产需缺口都将长期存在。在这一背景下,讨论我国农业“走出去”问题,始终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我国农产品的供求形势:大豆和油料作物是供给软肋
2007?2008年,全球粮食市场经历了一轮暴涨暴跌的“过山车”行情。粮价的波动,促使各国政府纷纷采取应对措施,也使人们认识到了世界范围内存在的粮食安全隐患。总体来看,在这一轮全球粮食危机中,中国受到的冲击尚不大,国内的农产品价格也基本保持了平稳。
这一形势的取得,与近年我国大力发展粮食生产的努力是分不开的。如图1所示,1998年,我国的粮食产量达到历史性高峰51230万吨,但到2003年又减至43065万吨,使粮食安全面临着较大的挑战。从2004年开始,随着一系列惠农强农政策的实施,我国粮食产量实现了连续5年增长,2008年达到52850万吨,创下了新的历史最高水平。对照来看,2008年我国的粮食净进口量为2881万吨,粮食自给率保持在了95%左右,这是我国粮食市场受国际粮价波动影响较小的重要保障。
但是,我们不能就此放松对粮食安全问题的警惕。一方面,近年我国粮食的连续增产,是多方面积极因素的共同结果,如果农业科技没有取得重大突破,今后继续增产的潜力是有限的。整体来看,我国从2004年开始成为粮食的净进口国,这一净进口的局面将长期存在。另一方面,我国农产品还存在结构性短缺,大豆和油料作物是我国农产品供给的软肋,据美国农业部的数据显示,2007/2008年度中国大豆的进口量达到了3781.6万吨,比上年度增加了20%以上,并且近10年来全球大豆进口的增量全部来自中国。图2清楚地显示了在我国谷物保持高比例自给的同时,大豆的自给率却在逐年下降。由于大豆是一种介于粮食和油料之间的农产品,在土地上和谷物之间存在着种植替代的问题,它的短缺同样会带来粮食安全问题。
农业“走出去”的理由和现状
一、到海外租地的理由
如前所述,我国农产品尚存在一定的产需缺口,尤其表现在大豆及油料作物上。目前我国的总人口还在继续增长,工业化城市化还将不可避免地占用一部分耕地,因此我国对农产品的进口需求将长期存在。但另一方面,由于全球范围内的粮食供求处于紧平衡状态,一旦再度出现2007?2008年这样的粮食危机,我国是否能按合理价格足量地进口到所需的粮食,是存在一定风险的。这种情况下,鼓励农业企业积极“走出去”,控制一定规模的海外农业生产能力,无疑具有战略意义。
从资源禀赋的角度看,在我国农地属于稀缺资源,而农业劳动力则有一定程度的富余。农地的稀缺性具体可由图3中土地成本的逐年增高得到印证,以大豆生产为例,在2000年我国的大豆生产成本中,土地成本远低于人工成本,由于土地成本提高的速度较快,到2007年已基本和人工成本持平了。此外,从农地流转的价格来看,目前东部沿海的农地租金最高可以达到每亩每年800元以上,这已是一个相当高的水平。
而对于一些地广人稀的国家来说,土地则是一种富余资源。例如,巴西共有可耕地面积2.8亿公顷,目前已耕种的仅占五分之一左右,非洲可开发的耕地面积达8亿多公顷,实际利用的也只有四分之一。如果到这些国家租地,并派出一定数量的国内劳动力进行农业生产,无疑能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
二、农业“走出去”的现状
首先从国外经验来看,日本和韩国同样是人多地少的国家,其在农业“走出去”方面的经验值得中国借鉴。
早在1899年,日本一家由官方资助的公司就向秘鲁派出了农场工人,这可以视作是日本农业“走出去”的开端。后来,日本东棉株式会社又在巴西的亚马逊河谷及圣保罗建起了农业聚居区。目前,日本在世界各地已拥有1200万公顷的农田,相当于日本国内农田面积的3倍左右。1978年8月,韩国政府为实施大米增产项目,在阿根廷购买了2万多公顷的土地。2008年4月,韩国又以提供无偿援助的方式,在蒙古获得了27万公顷的土地,这也是韩国规模最大的海外垦田项目。
我国也有相对较早的农业“走出去”实践。1996年,总部位于新疆的上市公司新天集团在古巴投资5万美元,播种了150公顷水稻,1998年新天集团又在墨西哥购置了1050公顷土地,累计投资320万美元。由于在这些土地上种植的单产远高于当地水平,因而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2007年中央“一号文件”第五部分的第三条提出,要“加快实施农业‘走出去’战略”,这表明农业“走出去”已上升为我国中央层面的决策。在2008年4月举行的“第二届中国企业跨国投资研讨会”上,农业部官员表示,国内企业赴海外开发战略性、短缺性农业资源,将弥补国内资源与需求间的矛盾,目前政府部门正在探讨相关鼓励政策。
从部分省区的情况看,各种形式的农业“走出去”项目正在如火如荼地开展。截至2008年7月底,广西有20多家农业企业到国外投资,投资总额达5亿元人民币。2004年3月,重庆市政府与老挝签订了“中国重庆(老挝)农业综合园区项目”合作协议,园区规划面积5000公顷,总投资498万美元,还计划输出1万名农业劳动力。截至2008年7月底,重庆市共批准境外投资农业的企业6家,投资总额1586万美元,其中中方投资为1486万美元。此外,像中粮集团这样的大型企业,也在南美、东南亚等地通过合资或并购的方式,积极地探索海外战略。
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全国在境外投资、合作的农业龙头企业有40多家,投资金额达153亿元,投资地区涉及亚洲、非洲、北美、欧洲、大洋洲的30多个国家和地区。此外还有不少尚未开始海外投资的农业企业也表达了“走出去”的意愿。
“走出去”所面临的挑战
农业“走出去”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面临着多方面的挑战。对于当前是否应大规模地实施,人们尚存有不少争议。总结起来,争议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风险是否可控,二是经济上是否可行。
第一方面,在海外从事农业经营面临着较大的风险。首先,这表现在社会安全上,目前我国大多数“走出去”的企业选择在非洲、南美洲等地区购买或租赁农场,这些地区的安全局势往往不太乐观,存在政局动荡、宗教和种族冲突及暴力事件多发等问题,这使海外农业经营面临很大的风险,甚至赴外人员的人身安全也面临威胁。
其次,风险还表现在企业经营上,位于非洲、拉美等地的投资东道国的基础设施、法律制度、农村组织化和市场化程度等方面可能都较为落后,同时由于国外投机资本的频繁进出,一些国家还会周期性地爆发金融危机,使得农业企业的经营风险大大增加。
最后,如果海外种地的目的是将所生产的粮食运回国内,那么当真正发生粮食危机时,还可能面临一种特殊的风险,即投资东道国为了优先满足本国需求而禁止粮食出口。或者,由于“走出去”的主体是企业,当粮价高涨时,企业出于利润最大化的考虑,不愿意按原计划将粮食卖回国内,而转售给其他出价更高的买主。事实上,定向销售到某一国的做法,本身是违背WTO自由贸易精神的。这些风险的存在,可能影响海外种粮初始目标的实现。
第二方面,“走出去”将产生不少额外成本,而农业投资的利润本来就不高,所以从经济的角度看可能并不合算。首先,在海外从事农业生产,无论是产前、产中还是产后都将增加许多环节。例如,需要土地租金及农田基础设施的建设费,国内人员到海外需要签证、交通及生活安顿,如果海外种粮最终是为了供应国内,那么还需加上运输及关税等成本。这种情况下,和国内生产相比,甚至和直接从国外进口相比,海外租地种粮都将具有成本劣势。其次,为了适应东道国的环境,需要培养和招募一大批熟悉当地法律制度、风俗文化、市场状况的专门人才,而且由于处在国外政府的管辖之下,税收和租金政策由所在国掌握,还可能导致成本波动。东道国政府出于自身利益或环保方面的考虑,往往会优先将劣等地出租给前来投资的企业,这将进一步导致经济上的不利。
此外,我国国内的农业生产能力尚有潜力可挖,使得国内的生产成本成为海外种粮的重要参照。尽管我国耕地资源十分紧张,但撂荒现象也时有发生,这主要是由种粮的比较效益低下引起的。例如,就在去年国际粮价持续大涨的时候,我国部分地区却出现了农民“卖粮难”问题,过低的粮价信号难以刺激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由于国内的农业经营成本低于“走出去”的经营成本,在大规模到海外租地种粮之前,应首先充分挖掘国内的粮食生产潜力,适当提高粮价,使农民能够对粮食供求作出准确的反应。
完善农业“走出去”的对策
尽管农业“走出去”面临着不少挑战,但在全球性粮食安全问题的阴影下,我国作为一个人多地少的大国,仍需将农业“走出去”作为一项长期战略。笔者认为,我们应采取以下几方面的对策,来保证农业能够顺利“走出去”。
第一,农业“走出去”需要由我国政府提供政治和外交方面的服务,同时“走出去”的农业企业自身也要积极地与当地的制度文化进行融合。海外的农业经营离不开东道国全方位的支持,因此我国政府应在外交上为农业“走出去”提供一个长期稳定的政治环境。同时,由于国外的法律制度、风俗文化往往与我国存在较大的差异,“走出去”的企业需全面掌握当地的法律制度,并融入当地文化以便充分调动当地雇员的积极性。
第二,在海外经营农业同样需要注重经济效益。固然,农业“走出去”有着保障国家粮食安全方面的考虑,因此付出一些额外成本是不可避免的。但这并不意味着海外的农业经营就可以不计成本,因为农业“走出去”主要还是以企业为主体来实施,本质上属于一种商业行为,如果在经济上不可行,这一行动就不可持续。我们必须避免农业“走出去”沦为经济上不合理的形象工程。
第三,“走出去”的农业经营品种应与国内的种植结构相协调,目前来看,海外应以种植大豆为主。尽管各种农产品在种植结构上可以互相替代,但它们对一国粮食安全的敏感度是不同的。一般来说,粮食作物的敏感度要高于经济作物,而在粮食内部,谷物的敏感度又要高于大豆。因此出于安全考虑,我国国内的农业生产应重点保障谷物供应,而“走出去”的生产则应以大豆和经济作物为主。
第四,海外的农业经营应同样可获得国家的农业补贴,同时应积极争取东道国政府的农业支持。目前我国在海外投资的农业企业,既不能享受国内对农业投资的优惠政策,也不能获得粮食直补、综合直补,农机具购置补贴等惠农补贴,这导致企业“走出去”的积极性受到影响。为使农业“走出去”的战略能顺利实施,国内的各项农业补贴也应覆盖这些企业,同时尽量简化海外投资的各种审批程序。另一方面,“走出去”的企业还应尽力熟悉和争取东道国的各种农业支持政策。
第五,应着力培育我国的大型农业跨国企业,并使之成为农业“走出去”的主力军。众所周知,ADM(Archer Daniels Midland)、邦吉(Bunge)、嘉吉(Cargill)和路易达孚(Louis Dreyfus)是世界知名的四大粮商,它们垄断了80%以上的全球粮食贸易量。这四家粮商的分支机构遍布全球,根据形势变化不断地调整着自己的业务区域,并且都具有百年以上的跨国经营历史。我国国内的粮食企业与之相比,不但规模偏小,海外机构尚不健全,而且从事海外经营的经验也不足。我国要顺利实施农业“走出去”战略,培育大型农业跨国企业应是一项重要举措。http://www.grainyq.com